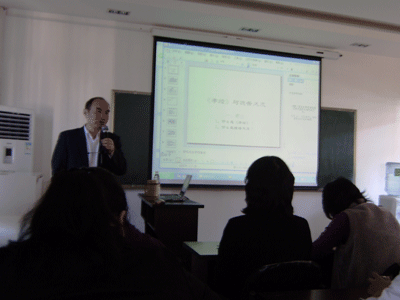
11月7日下午三点,在文科楼424教室举行了古籍整理研究所儒藏系列讲座第四十五讲,本次讲座由古籍所所长,儒学专家舒大刚教授主讲“《孝经》与魏晋风度”。舒大刚教授长期从事儒学研究,有许多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问世,由其主编的《儒藏》前期成果已经在学术界赢得很好的声誉。目前,舒教授正在从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《中国孝经学史》的研究,本次讲座,他带来了其在研究过程中的许多心得体会。
《孝经》崇尚孝道、尊重礼法,魏晋风度率真任诞、不守礼法,其内涵相差天远,讲座首先以幻灯片的形式罗列了《孝经》与“玄言”的七大矛盾:
《孝经》主敬,玄言轻薄
《孝经》主礼,玄言非礼
《孝经》主爱惜身体,玄言伤身
《孝经》主忠,玄言主隐
《孝经》主谏诤,玄言不臧否人物
《孝经》重丧,玄言随意
《孝经》建功,玄言任性
然而经过研究,这两者除了具有许多明显的矛盾外,其背后是有相通之处的。名士们不拘礼教,崇尚自然,超然物外,好《老》《庄》,视功名富贵为浮云,对世俗礼法极端蔑视,积极追求精神上的超脱,一时之间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与慰藉。但这种满足与慰藉是极其短暂的,往往在前后代传承之中改变了其本来的面貌,以至于父辈常常不愿自己的子女也走上率真任诞的魏晋风度之路,如阮籍就曾告诫自己的儿子阮浑。这就是所说的魏晋风度之“任诞流弊”,然而与此同时,《孝经》所构建的伦理制度却在不温不火的承载着整个社会的运作,并以此而代代相传,于是两者之间最本原的属性就突现出来了,借用阮籍哭兵家之女的话说便是:“其外坦荡而内淳至。”这就是魏晋风度与《孝经》的相通之处:“人之本性”。
玄学家也是有具有孝心,具有人性的。阮籍认为:“禽兽知母而不知父,杀父,禽兽之类也,杀母,禽兽之不若。”虽然这样的表述方式极端残酷,但它至少说明了此中也是有人性的。后来阮籍母亲去逝,他虽依然不按礼法行事,但从他多次呕血的精神状态上来看,母亲的去逝,他的内心也是相当痛苦的,那么,这就已经表现出了“孝”。
同样,嵇康说:“吾每读尚子平台《孝感传》,慨然慕之,想其为人。”“今但欲守陋巷,教养子孙。”王衍丧子之后,悲不自胜,说:“圣人忘情,最下不及于情,然则情之所钟,正在我辈。”这些都表现出魏晋名士的“本性”之中也有“孝”的一面。
在这样的社会意识背景支持下,虽然表面上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的魏晋风度占据着历史的主流,但对礼法的崇尚,对“孝”提倡也发展得很快。讲座从“打击不孝”、“奖励孝悌”、“清议舆论”、“孝子辈出”等几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诠释与补充:1魏晋时期传授《孝经》比汉代更加普遍,设立了《孝经》博士、助教,并纳入考核系统;2皇帝、太子、诸侯带头学《孝经》、注《孝经》、讲《孝经》成为风气,形成皇家《孝经》学现象,并有一百多家的《孝经》研究成果流传下来;3出现了仿《孝经》而作其他经典、神化《孝经》的现象。这些都表明,在当时,提倡《孝经》已经成为一种风气,《孝经》的流传十分广泛。
在讲座的最后,舒老总结道:“总而言之,尽管玄学之风兴盛、魏晋风度流行、礼法之士被讥讽、礼仪制度受挑战,但这一时期仍然对讲人类本性,讲父子之道,讲‘夫孝,天之经,地之义,民之行也’这样一种经典是尊重的、是研究的。《孝经》说的是人的本心,言的是人的本行,它所归纳的也是我们人之为人、家之为家、社会之为社会、国之为国的根本性的内容,所以《孝经》不可卑,孝道不可丢。”
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之中,讲座圆满结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