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成都行》
陆 游
倚锦瑟,击玉壶,吴中狂士游成都。
成都海棠十万株,繁华盛丽天下无。
青丝金络白雪驹,日斜驰遣迎名姝。
燕脂褪尽见玉肤,绿鬟半脱娇不梳。
吴绫便面对客书,斜行小草密复疏。
墨君秀润瘦不枯,风枝雨叶笔笔殊。
月浸罗袜清夜徂,满身花影醉索扶。
东来此欢堕空虚,坐悲新霜点鬓须。
易求合浦千斛珠,难觅锦江双鲤鱼。

《全蜀艺文志》(全二册)
《全蜀艺文志》是明代杨慎编的一部有关四川的诗文选集,对于研究四川的历史与文化来说,这是一部案头必备的基本典籍。
杨慎,字用修,号升庵,四川新都人,他的故居就在今新都名胜桂湖边上,现在那里还有杨升庵祠。杨慎博学高才,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学者。《明史》本传说: “明世记诵之博,著作之富,推慎第一。”俞廷举《全蜀艺文志序》曰:“余尝与天下士论古今真大才子,得三人: 一曰唐太白,一曰宋东坡,一曰明升庵。”“升庵以翩翩公子生相门,金殿传胪,为天下第一人,较李、苏为得意。尤西堂《登科记》以太白天上及第,谓状元中以有太白重,太白不以状元重。然则升庵岂非状元中以有其人为重者哉! 学问渊博,平生著作如林,大小凡三四百种。”据记载,杨慎著述多达四百余种,已经整理成书、见于著录的也有二百余种。《全蜀艺文志》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。
杨慎在其漫长的流放生涯中曾经有七次返蜀,嘉靖十八年他第五次返蜀。二十年,四川巡抚刘大谟发起重修《四川总志》,遂礼聘杨慎与王元正(字舜卿)、杨名(字实卿) 担任编纂工作,开局于成都城东静居寺宋濂、方孝孺祠。杨名修《建置》《山川》等志;王元正修《名宦》《人物》等志;杨慎修《艺文志》。《艺文志》“始事以八月乙卯(初二) 日,竣事以九月甲申(初一),自角匝轸,廿八日以毕”。据杨慎说,他曾“嘱乡进士刘大昌、周逊校正而付之梓人”,似乎曾刊印过单刻本。《四川总志》初稿完成后,刘大谟对杨名、王元正所修的部分不甚满意,于是又嘱按察司副使周复俊、佥事崔廷槐统一体例、调整门目、笔削内容、重加编定,“而《艺文志》则悉仍升庵之旧,未之能易焉”(崔廷槐《四川总志后序》)。这部修定过的《四川总志》刊于嘉靖二十四年。《总志》仅十六卷,以杨慎所编《艺文志》六十四卷附于其后,别题为《全蜀艺文志》。
全收录全面• 历久弥新
《全蜀艺文志》收录诗文一千八百七十三篇,有名氏的作者六百三十一人。是书选录的范围以与蜀有关为准,不论作者是否蜀人,但“若蜀人作仅一篇传者,非关于蜀亦得载焉”。“诸家全集,如杜与苏,盛行于世者,只载百一。”《全蜀艺文志》所收诗文以唐宋最多,明人的作品收得很少,仅九十余篇,包括杨慎父亲的诗文三篇。他说: “同时年近诸大老之作,皆不敢录,以避去取之嫌。”
全书诗文按文体编排,篇次则以作者的时代先后为序,前五十卷的文体门类大体沿袭《成都文类》,但“诗”中增加了“诗余”(词)一类。后十四卷世家、传、碑目、谱、跋、行记等则为杨慎新添。杨慎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二十八天之中辑录到这么多的作品,主要是由他父亲原来所收集的材料作为基础。他在本书序言中说: “先君子在馆阁日,尝取袁说友所著《成都文类》、李光所编《固陵文类》,及成都丙丁两记(按: 指范成大《成都古今丙记》、胡元质《成都古今丁记》)、《舆地纪胜》一书,上下旁搜,左右采获,欲纂为《蜀文献志》而未果也。悼手泽之如新,怅往志之未绍……乃检故簏,探行箧,参之近志,复采诸家。……支郡列邑,各以乘上,又得汉太守《樊敏碑》于芦山,汉孝廉《柳庄敏碑》于黔江。……唐宋以下,遗文坠翰,骈出横陈,实繁有昈,乃博选而约载之。”
在追索各篇的材料来源时,也证实了本书的取材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: 一是《成都文类》;二是《固陵文类》;三是《文苑英华》;四是唐宋人文集;五是《舆地纪胜》与《方舆胜览》;六是地方志,包括上述成都丙、丁两记。元费著在宋《庆元成都志》基础上重修的《至正成都志》,以及明代四川地方志。书中的碑刻、题记大概都是出自明代地方志。以上取材来源当中,有好些书现已失传,这就使得《全蜀艺文志》一书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。据统计,在本书所收的一千八百余篇诗文中,有三百五十余篇不见于其前的文献。换句话说,这三百五十多篇诗文全靠《全蜀艺文志》才得以保存下来。
“另类”的选文标准•超高的文献价值
《全蜀艺文志》之所以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,还在于杨慎选录诗文的标准与一般诗文选集有所不同。一般诗文选集主要从文学的角度来进行选择,而杨慎的视野则更为广阔,他更注意于诗文的史料价值。也就是说,他更注意从史志的角度来选文。因此,在此书中选入了不少为一般诗文选家不屑于选录的似乎很“另类”的、却又非常重要的文章。例如范成大的《益州古寺名画记》(此文很可能是范成大《成都古今丙记》的一部分),其中开列了淳熙间仍保存于大慈寺的唐宋名画,完完全全是一篇账单式的文字。它虽无文彩可言,却是四川古代绘画艺术史上的一篇重要数据。像这样的例子还不少。
我们再以《全蜀艺文志》与《成都文类》比较。《成都文类》也有很高的文献价值,但选文的标准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框框,主要以文学的标准来选文,这从袁说友的书序可以看出。单就这一点来说,袁说友的眼光显然比不上杨慎。我们在前面已谈到,《全蜀艺文志》较之《成都文类》,增加了世家、传、碑目、谱、跋、行记、题名等文体,这说明前者收文的范围较之后者更为广泛。在这些文体下所收录之文,多是珍贵的四川史资料。如卷五三至卷五七所收的费著七谱:《氏族谱》《器物谱》《笺纸谱》《蜀锦谱》《钱币谱》《楮币谱》《岁华纪丽谱》,系统地纪录了宋代成都的士家大族,新获文物,笺纸的名品,蜀锦的生产与花色,钱币的铸造与流通,纸币的发展与发行,以及岁时节日的盛况,对研究宋代四川的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风俗具有重要的价值。
《全蜀艺文志》一书以其文献价值,使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宝库中占有一席之地。正如俞《序》所言:“凡能拾人遗文残稿,而代存之者,功德当与哺弃儿、埋枯骨同。夫以本地之文献,本地之人,尤当爱惜而表章之。”当然,此书也还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,但这些缺点错误都只是大醇小疵,瑕不掩瑜。
刘琳、王晓波点校《全蜀艺文志》初版于2003年5月由北京线装书局出版,至今已过去19年。此次纳入《巴蜀全书》,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再版。再版对初版作了较大修订,大致统计修改了正文标点300余处,改正正文讹、脱、衍、倒230余处,改动正文的分段48处,修改得最多的是校记,共计800余条。其中有大量的考证,有的条文达二三百字,书末附录的《引用书目》也有所增补。另外,按照现行的用字标准和出版要求,再版对旧字形做了处理,对异体字做了规范,对用字做了统一。通过这次对初版的补充修正,本书的学术质量有了较大提高。
《全蜀艺文志》•序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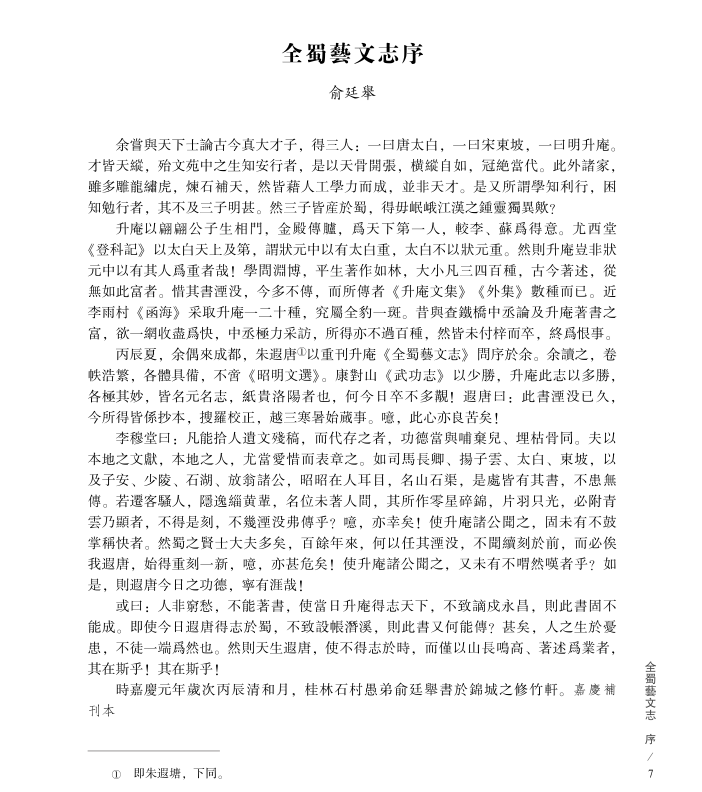
整理者•简介
刘琳,男,1939年生,贵州丹寨人,四川大学教授。195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,留系任教。讲授过中国历史文选、古代汉语、中国古文献学、古籍整理学等课程。1984年调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任副所长。曾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常务理事、荣誉理事,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,2001年退休。主要从事的学术研究领域为古籍整理研究、中国中古史。在古籍整理学、魏晋南北朝史、宋代文史、道教史、四川史、西南民族史等方面均有很大成就。独撰、合撰、主编的学术专著及古籍整理著作达1亿2千余万字,包括《华阳国志校注》《三国志选译》《四川古代史稿》《现存宋人著述总录》《中古泥鸿》《范仲淹全集》《黄庭坚全集》《全蜀艺文志》《古籍整理学》《全宋文》(主编)、《成都文类》《宋会要辑稿》等。发表论文50余篇。
王晓波,男,1948年生,重庆江津人。四川大学研究员。1976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,留系任教,讲授先秦文学史及作品选。1985年调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,1990年任该所副所长。2009年调任四川大学图书馆副馆长。出版专著:《冠准年谱》《宋辽战争论考》《宋四家词选译》;主编《清代蜀人著述总目》《四川大学馆藏珍稀地方志选编》第一辑;古籍整理专书有《全蜀艺文志》《景定建康志》、民国《华阳县志》、民国《双流县志》《锦江书院志》、多种《丹棱县志》等;为《全宋文》编委之一,承担完成包括25个宋人别集在内的700余万字的校点,还参与《宋会要辑稿》的校点整理。发表论文40余篇。